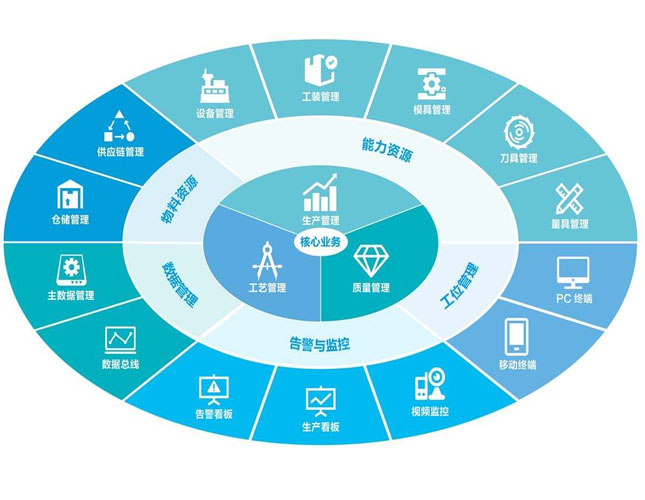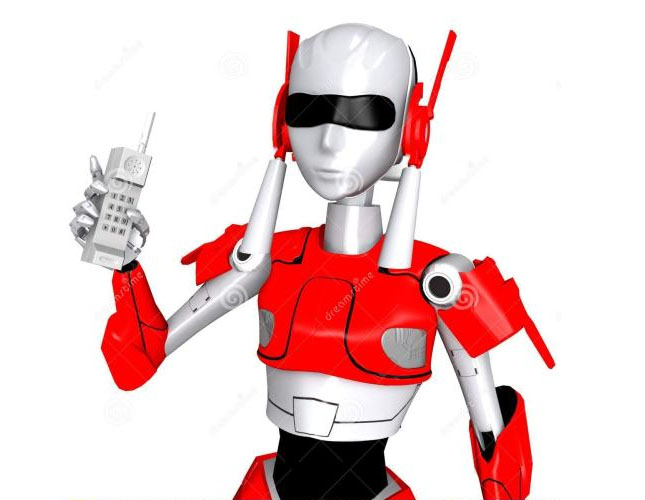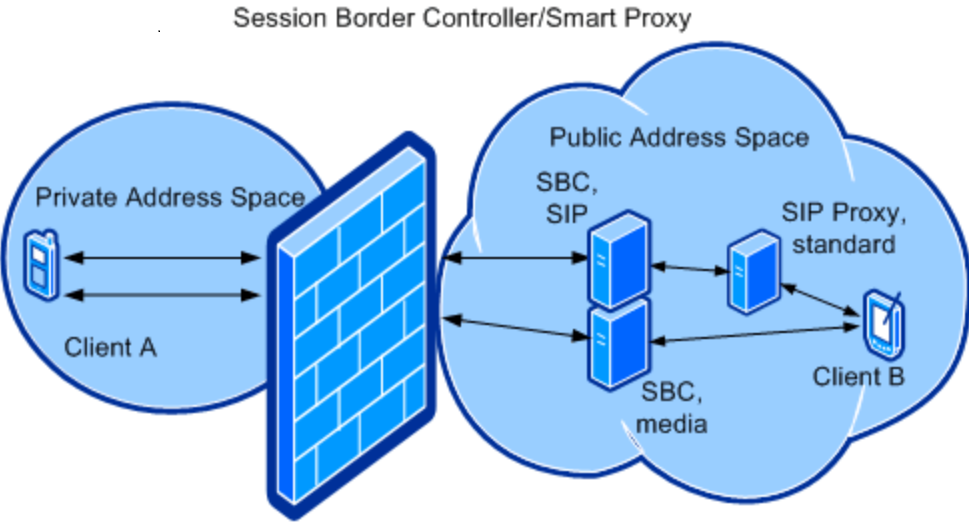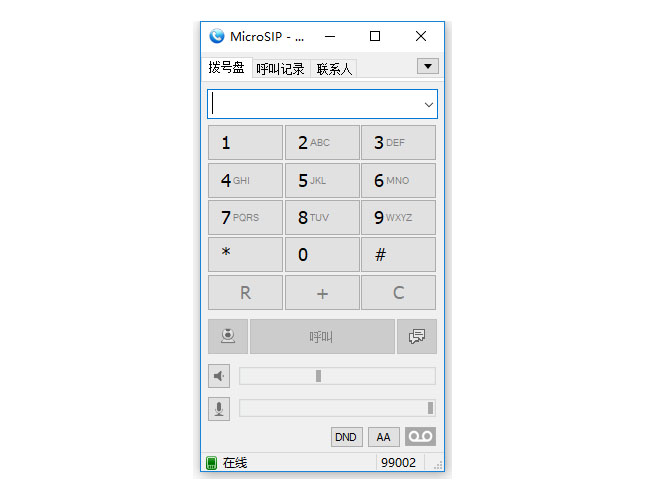(一)一自我认同感的确立
比起其他的心愿而言,人们更希望得到的是被理解。它超越了性、惧怕丧失和遗弃,希望被理解和接纳是最为接近人需要的本质的。在人的一生中,我们是从他人的眼神中读出我们对他人的意义的。我们注视的目的是要把他人的眼睛作为我们自己体验的镜子;通过体验我们的愿望、感觉和思想,通过从他人身上唤起的反应,我们了解自己并学会整合自己。这种试图从他人的眼中看出自身重要性的需要,是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建构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在我们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从未终止过这种从他人眼中获取无条件的、坦率评价的需求。被理解的需要也因此被确认为是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它决定了一个人将来所拥有的自我价值,我们从没有像被理解时那样感到自我的完整性。
然而,很矛盾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被完全了解过。
母亲对她的孩子所传递的体贴和赏识是自我意识的最初来源。和一个有回应的人进行目光接触会让我们对自己的体验能够确信,让我们感到我们确认了自己是谁,也决定了我们可以相信自己什么。一旦获得了充足的回应,婴儿就开始发展自我意识,并且开始踏上发现自我本质,展现自我风采的漫漫人生探索之路。
渐渐离开婴儿所拥有的那种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其存在本身的、无条件的、爱的环境,儿童会发现爱与接纳原来是有规范和条件的。一旦儿童能在认知层面上建立起行为与他人反应之间的联系,他们就开始想要弄清楚母亲的赞成与否的含义是什么。一些儿童只能理解这种解释:“当妈妈看起来很恼火,在那儿发牢骚、批评我,并且面无表情的时候,那就一定意味着我是个坏孩子。”这种反复出现的拒绝情境就能够严重毁掉
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对于这种否认的理解也可能会危及其他关系维度的联系:“妈妈讨厌我,所以她会离开我!”拒绝使得任何一种个体能够调用的应对资源或者防御都成为必要的。这是一种非常实在的在他人眼里寻求赞赏的努力。儿童会努力与其他个人对他“是什么、想什么、感到什么、甚至需要什么”的要求相适应。结果,成长中的儿童压抑了真实客观的感受,把自己塑造成具有良好社会化容纳性的人。一旦个人的行动只是对其他人的要求或者愿望作出反应,那么这个人的发展与其说是个人自身核心品质的展示,不如说是成为环境的延伸。非真实自我从放弃他们的本性去取悦他们的父母时就开始发展了。对这种极为重要的交流的解释成为人格发展的核心任务。
如果儿童能够区分“我不喜欢你正在做的事情”和“我不喜欢你”之间的区别,或者母亲能够很好地表达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儿童就能够调整那些他们不受欢迎的行为,而不影响自我意识。
在青春期,构建自我是基本的发展任务。在此阶段,问“我是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问谁能理解青少年自己认为的“自我”,谁能够了解并容忍他们的新情感,谁能够知道他们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就是青少年们发自内心的充满抗争的呼喊“你们不理解我!”
因此,来自他人的情感、重视以及接纳的反应是非常重要的情感营养素。没有这些我们将不能成为我们。这些营养素使我们有勇气在他人面前展示自己,呈现真实的自我,使我们愿意停留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
(二)理想化他人
理想化是一种吸引我们趋向他人以便拥有或者内化他们品质的心理过程。这个领域的关键是借助于追随某人进入一个新的、可能只是被模糊感觉到的现实中去,并通过某种方式利用某人来扩展自我。我们可能会指望别人来扩展我们的意识,我们也可能希望用某种方式拥有另一个人的完美,或者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认同并试图变得像我们敬仰的某个人。这些体验中的任何一种都引起了我们对他人品性的注意,这些品性引起了自我的调整。
婴儿早期,深深藏在神话与个体心灵之中的是一种关乎无所不能的完美意象,在这种意象里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婴儿时期的全能感。在这一阶段婴儿怀有这样一种信念—他们能够要求完全的注意与满足。但是这种全能感很快就让位于对自我局限性的认识。懊恼于自己的不完备,并且仰赖他人的能力给自身的安全保障。自己可能并非无所不能,但有朝一日,希望自身也能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从儿童的视角来看,问题就成为如何参与父母的那种无所不能并且拥有它。为了能参与这种力量或者能控制这种力量,一种可能性就是努力去取悦父母并和他们结合起来。儿童会在意识层面努力争取变得像他们的父母或父母理想中的形象一样,做那些他们力所能及的值得别人敬重的事情。
顺利度过俄狄浦斯期之后,理想化就成为对我们自己的脆弱和缺乏知识的回应;我需要相信其他某个人拥有我们所没有的控制力。
年轻人,通常是在青春期,开始努力达成一个协定:宁愿拥有真实的父母,而非那种理想化的,父母越来越失去理想化的色彩;但是,他们也仍然会搜寻那些似乎拥有父母曾经详细描绘过的理想化的品性的人。
一个理想化他人的出现是件令人兴奋激动的事情,因为这将预示着我们自己与完美幻想再次结合的可能性。
对于成长而言,理想化是必要的。只有存在理想化,才会对远景进行展望或者对自我与限制因素的边界的超越有一种快乐的感觉。
一且我们把他人理想化了,我们自己也就通过与他们或者他们的某种象征之间的联系而获得鼓舞。我们需要英雄,我们渴望与他们有所联系。但是不像那种现实的接近,我们寻觅可以依恋的人物,在我们与那些我们理想化了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上经常存在一种神秘的因素。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承载着特殊的意义;我们的存在是因为他们存在于一个特殊的层面上。
青少年只要一和他们的偶像接触就会感到自己更加有张力了。“他看着我”或者“他触摸了我”,通过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得到了保佑,精力充沛起来,也更有力量了。
另一种拥有理想化他人的方式是通过认同来达到的。我们能够通过变得和那些我们所爱慕和看重的人相似来“拥有”他们。因此,他人就成为自我某些方面未来的蓝图。
反向认同就是不要变得相似的一种愿望。人们频繁地和那些在我们意识层面被予以否认的、强烈的无意识层面的认同进行斗争。
反向认同可能是一种强烈的联系形式。我们不希望自己像某人的需要,也是一种终生承载着那个人意象的方式。
理想化他人实际上就是一种危险与机遇并存的关系过程。
比起其他的心愿而言,人们更希望得到的是被理解。它超越了性、惧怕丧失和遗弃,希望被理解和接纳是最为接近人需要的本质的。在人的一生中,我们是从他人的眼神中读出我们对他人的意义的。我们注视的目的是要把他人的眼睛作为我们自己体验的镜子;通过体验我们的愿望、感觉和思想,通过从他人身上唤起的反应,我们了解自己并学会整合自己。这种试图从他人的眼中看出自身重要性的需要,是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建构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在我们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从未终止过这种从他人眼中获取无条件的、坦率评价的需求。被理解的需要也因此被确认为是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它决定了一个人将来所拥有的自我价值,我们从没有像被理解时那样感到自我的完整性。
然而,很矛盾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被完全了解过。
母亲对她的孩子所传递的体贴和赏识是自我意识的最初来源。和一个有回应的人进行目光接触会让我们对自己的体验能够确信,让我们感到我们确认了自己是谁,也决定了我们可以相信自己什么。一旦获得了充足的回应,婴儿就开始发展自我意识,并且开始踏上发现自我本质,展现自我风采的漫漫人生探索之路。
渐渐离开婴儿所拥有的那种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其存在本身的、无条件的、爱的环境,儿童会发现爱与接纳原来是有规范和条件的。一旦儿童能在认知层面上建立起行为与他人反应之间的联系,他们就开始想要弄清楚母亲的赞成与否的含义是什么。一些儿童只能理解这种解释:“当妈妈看起来很恼火,在那儿发牢骚、批评我,并且面无表情的时候,那就一定意味着我是个坏孩子。”这种反复出现的拒绝情境就能够严重毁掉
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对于这种否认的理解也可能会危及其他关系维度的联系:“妈妈讨厌我,所以她会离开我!”拒绝使得任何一种个体能够调用的应对资源或者防御都成为必要的。这是一种非常实在的在他人眼里寻求赞赏的努力。儿童会努力与其他个人对他“是什么、想什么、感到什么、甚至需要什么”的要求相适应。结果,成长中的儿童压抑了真实客观的感受,把自己塑造成具有良好社会化容纳性的人。一旦个人的行动只是对其他人的要求或者愿望作出反应,那么这个人的发展与其说是个人自身核心品质的展示,不如说是成为环境的延伸。非真实自我从放弃他们的本性去取悦他们的父母时就开始发展了。对这种极为重要的交流的解释成为人格发展的核心任务。
如果儿童能够区分“我不喜欢你正在做的事情”和“我不喜欢你”之间的区别,或者母亲能够很好地表达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儿童就能够调整那些他们不受欢迎的行为,而不影响自我意识。
在青春期,构建自我是基本的发展任务。在此阶段,问“我是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问谁能理解青少年自己认为的“自我”,谁能够了解并容忍他们的新情感,谁能够知道他们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就是青少年们发自内心的充满抗争的呼喊“你们不理解我!”
因此,来自他人的情感、重视以及接纳的反应是非常重要的情感营养素。没有这些我们将不能成为我们。这些营养素使我们有勇气在他人面前展示自己,呈现真实的自我,使我们愿意停留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
(二)理想化他人
理想化是一种吸引我们趋向他人以便拥有或者内化他们品质的心理过程。这个领域的关键是借助于追随某人进入一个新的、可能只是被模糊感觉到的现实中去,并通过某种方式利用某人来扩展自我。我们可能会指望别人来扩展我们的意识,我们也可能希望用某种方式拥有另一个人的完美,或者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认同并试图变得像我们敬仰的某个人。这些体验中的任何一种都引起了我们对他人品性的注意,这些品性引起了自我的调整。
婴儿早期,深深藏在神话与个体心灵之中的是一种关乎无所不能的完美意象,在这种意象里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婴儿时期的全能感。在这一阶段婴儿怀有这样一种信念—他们能够要求完全的注意与满足。但是这种全能感很快就让位于对自我局限性的认识。懊恼于自己的不完备,并且仰赖他人的能力给自身的安全保障。自己可能并非无所不能,但有朝一日,希望自身也能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从儿童的视角来看,问题就成为如何参与父母的那种无所不能并且拥有它。为了能参与这种力量或者能控制这种力量,一种可能性就是努力去取悦父母并和他们结合起来。儿童会在意识层面努力争取变得像他们的父母或父母理想中的形象一样,做那些他们力所能及的值得别人敬重的事情。
顺利度过俄狄浦斯期之后,理想化就成为对我们自己的脆弱和缺乏知识的回应;我需要相信其他某个人拥有我们所没有的控制力。
年轻人,通常是在青春期,开始努力达成一个协定:宁愿拥有真实的父母,而非那种理想化的,父母越来越失去理想化的色彩;但是,他们也仍然会搜寻那些似乎拥有父母曾经详细描绘过的理想化的品性的人。
一个理想化他人的出现是件令人兴奋激动的事情,因为这将预示着我们自己与完美幻想再次结合的可能性。
对于成长而言,理想化是必要的。只有存在理想化,才会对远景进行展望或者对自我与限制因素的边界的超越有一种快乐的感觉。
一且我们把他人理想化了,我们自己也就通过与他们或者他们的某种象征之间的联系而获得鼓舞。我们需要英雄,我们渴望与他们有所联系。但是不像那种现实的接近,我们寻觅可以依恋的人物,在我们与那些我们理想化了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上经常存在一种神秘的因素。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承载着特殊的意义;我们的存在是因为他们存在于一个特殊的层面上。
青少年只要一和他们的偶像接触就会感到自己更加有张力了。“他看着我”或者“他触摸了我”,通过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得到了保佑,精力充沛起来,也更有力量了。
另一种拥有理想化他人的方式是通过认同来达到的。我们能够通过变得和那些我们所爱慕和看重的人相似来“拥有”他们。因此,他人就成为自我某些方面未来的蓝图。
反向认同就是不要变得相似的一种愿望。人们频繁地和那些在我们意识层面被予以否认的、强烈的无意识层面的认同进行斗争。
反向认同可能是一种强烈的联系形式。我们不希望自己像某人的需要,也是一种终生承载着那个人意象的方式。
理想化他人实际上就是一种危险与机遇并存的关系过程。